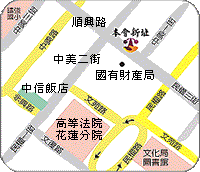看見資本主義社會的一道曙光
加拿大政治學者Will Kymlicka曾說:「當人們自己的母語在公共領域內不被重視,甚至是被歧視的時候,他們會感覺到這是對他們自我認同的一種傷害。」長期以來,台灣原住民族因為殖民政府或移民社會的政治優勢,而被迫放棄母語,而因為無法在公共領域使用母語表達,原住民族也漸漸否定他們的文化和尊嚴,最後因為整個社會都是優勢民族的文化以及為優勢民族所制訂的法令,於是原住民族有些學習障礙以及認同的問題,當然以上種種的惡性循環,就讓他們順理成章的變成了弱勢民族。
法律扶助基金會花蓮分會自去年七月一日成立以來,也從受理的法律扶助申請案件的統計數據,發現了原住民朋友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弱勢處境,在短短八個月的時間,法扶會花蓮分會共受理約290件原住民申請法律扶助案(申請案件總量為848),遠遠超過原住民族在花蓮地區的人口比例,其中,他們所遭遇的法律問題以下列三種為多數:(一)家庭暴力或其他理由所造成的離婚及子女監護權的問題(二)違法解雇或領不到工資的勞資糾紛(三)原住民保留地糾紛。而這三大類型的法律糾紛適足以說明弱勢民族因為優勢民族的教育、政策、法令及社會結構性等問題,所被邊緣化的弱勢地位,但這次我們想先跟讀者分享一個實際發生在法扶會的勞資爭議個案。
一群原住民勞工的的故事
初見他們時,黝黑的臉上掩不住的急切與慌亂,我們似乎也從他們的眼神中感染了那份無助。和以往我們所處理過的原住民勞工案件一樣,又是資方利用勞方弱勢貧窮的處境,而心存僥倖的不正義行為,我們相信,貧窮也許會使得部分人不能有效實踐他們的權利,但不表示他們的人權就可以任意的被剝奪。眼前的這十數位的原住民男性,他們有些在包商雇用並做完工程後卻領不到任何工資;而有的人則是小工頭,包商做工程時告訴他們「要錢要人都好商量」可是真正當完工後,包商不是哭窮,就是不見人影。
面對他們急切的心情,不禁使我們想起去年八月份在蘭嶼受理的達悟族朋友的法律扶助申請案件,這些單純質樸的原住民朋友,他們多半是最底層的勞動階級,平常多以打零工維生,而家中老老小小也都仰賴這些打零工的錢過日子,但最後他們期待可以領取的工資,卻隨著工程的結束全部落到資方的口袋裡,他們悲傷、失望、無助,不過也僅僅是如此,明天過後,他們仍得重拾心情,再尋找其他打工的機會,至於求償?跑法院?「唉!沒時間啦,家裏老婆孩子還等著用錢呢!打官司,不知道要等到哪一天才能拿到,就讓那些有空的人去打吧!」有些同行的受害工人操著口音甚重的國語說道。當然,有些境況比較好的,巴望著能早早領到這筆錢,還願意四處奔走尋找可能的管道來解決。
「實在沒辦法啦!也試過什麼勞資協調,沒有用!大老闆就是不肯出面,只能去告他們了。」帶其他人來申請的工頭氣憤的說道,對於這樣的一段話,我們一點也不感陌生,有許多的勞資糾紛案件,不論受害的是個人或一群人,不論受害的事實是違法解雇、領不到工資、或職業災害等,資方的態度多半是不聞不問,冷漠及沈默有時候可以讓勞方不戰而退,但有時候也會激起勞方宣戰的決心,而我們的立場是以公權力的介入來緩和或縮小勞資階級的對立與差距,進而改善弱勢朋友的處境。
在踐行了必要的法律扶助申請手續後,我們的審查委員依據法律扶助法的規定,在審酌這些申請人所提出的財產證明資料及案件事實的證據資料後,一致認為他們確實為法扶會所要幫助的無資力及權益被侵害的弱勢民眾,而通過他們的法律扶助,我們也旋即為這些受害的勞工朋友指派扶助律師進行訴訟事宜。
然案件通過扶助後,「包商沒有錢』、『上游廠商不想認帳』…,不妙的消息一個個傳來,這些來自受扶助人私下探訪所得的消息,一再削弱他們對於提起本件訴訟的信心,固然本件訴訟的相關證據十分充分,且極有可能獲得勝訴判決,但如果僅僅只是獲得幾頁勝訴的判決書,而完全無法取回一分一毫,似乎又和他們所期待的正義結果差距太多,遲來的正義或沒有任何果實的正義,對於他們而言是沒有任何實益的。正當案情陷於膠著的時候,本件的扶助律師因為長期在台北縣市為弱勢勞工團體處理勞資爭議案件,有豐富的談判及協調經驗,於是他主張再一次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把包商、上游廠商都找來一起協商,這樣拿到錢的機率還大些。
只是,最簡單的反而最難,正當扶助律師凡事都已準備完成了,卻發生了一個問題,『當事人不知道跑哪去了!!!』律師只差沒有急得跳腳!『不知道你們找當事人會不會比較好找一點?我一直都聯絡不上他們!可是勞資調解又得當事人出面,我每天做夢都會驚醒,怕這件案子會超過時效!萬一徒勞無功,我乾脆把錢退給基金會,不承辦這件案子好了』扶助律師不知道這些原住民朋友為了養家餬口,像侯鳥一樣的居無定所,他們有些人在高雄工作,有些在宜蘭工作,於是,我們努力的和他們取得聯繫,並採取「緊迫盯人戰術」,但發現即使我們再三告誡他們的家人務必轉達這件事情的急迫性與嚴重性,可是他們的家人仍是一派悠閒的告訴我們『好啦!好啦!我會告訴他們的啦!』之後就音信杳然了。
在歷經了幾個月的輾轉周折後,終於聯絡上了受扶助人,也敲定了勞資調解的時間。在前一天確認受扶助人已確定得知隔天要去調解,並且也知道地點、時間後,原以為可以鬆口氣…沒想到還是有波折!『現在已經十點了,沒有看到當事人啊!』接到了扶助律師的電話,我們禁不住焦急起來,在打電話給本件受扶助人的代表後才發現他還在家裏!『你怎麼還沒去調解?!』忍不住大聲的問他,『唉呀!調解沒有用啦,那個小老闆我也認識,所以我跟他約下午啦!』他的語氣仍是那麼輕鬆悠閒,但明顯可知他對於我們這個政府所設立的公益性機構一點信心也沒有。我們的承辦專員再次忍不住大聲起來『這個扶助律師是勞工法的專門律師,你要聽他的啦!而且他和縣政府的人已經在那裏等了,趕快去!!』他才不情願的出門。有時候,適時的表達我們的憤怒,確實也可以讓法律扶助的過程更加順暢,因為有些受扶助人會突然變得清醒。
這次的勞資爭議協調,扶助律師不僅將包商及上游營造公司納入協議,更將發款公司也放進來,明訂「在支付XX公司工程款時,應先支付當事人XXX等人之欠款。」且不僅是通過扶助的原住民朋友可以依據決議請求資方給付工資而已,還包括了其他受害的當事人。『如果這樣還拿不到錢,就算訴訟也不可能拿到錢了』扶助律師語氣裏掩不住的喜悅。照這樣看來,目前已經是最好的結果了…一切惟有到拿錢的那一天才能見真章了…。
正義論的作者羅爾斯曾說:「人人均應受到平等的對待,享用同等的資源,儘管如此,我們都無法也無須刻意消除這種先天才能的差異,追求絕對的結果平等,因為還有更好的選擇:社會可以善用優勢者的才能,更有效地改善所有人的處境」這一次扶助律師的成功出擊,讓我們更加相信,法律扶助是一個利用優勢者來改善弱勢者處境的社會正義重分配的有利工具。
法扶會花蓮分會執行秘書蔡雲卿律師
2007年10月8日 星期一
看見資本主義社會的一道曙光
張貼者: 法律扶助基金會花蓮分會 於 10/08/2007
分類: B.法扶廣場